|
网课百象:家境好的在群里活跃,贫困学生多数在请假劳作时间:2020-07-11 过去的半年,为了应对疫情,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开始网络授课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以往课堂上被遮蔽的某些事实,开始被网络撕开、放大,推到每个人面前。在张秋子的网课记录中,我们发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图丨视觉中国 这是一位大学老师的网课记录。 张秋子是云南昆明人。完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业后,她回到家乡,成为文学院的青年教师。从就读的一线城市高校来到这所地方师范院校后,她一头撞上结结实实的生活。这所高校的生源基本来自云南省内,超过半数的学生出身村寨乡镇。如何在并不理想的基础教育之上,展开她的文学教育?如何面对学生花大力气理解但丁或莎士比亚,最终却是去当小学语文老师? 刚刚过去的半年,为了应对疫情,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开始网络授课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以往课堂上被遮蔽的某些事实,开始被网络撕开、放大,推到每个人面前。在张秋子的网课记录中,我们发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对不起老师,我家被偷了,请不要点我回答问题,因为我在派出所做笔录。 一个周三的下午,我开始带领同学们读诺贝尔奖得主石黑一雄的《远山淡影》。 上周的这个时候,我们刚读完了黑人女作家托尼·莫里森的《最蓝的眼睛》。莫里森的小说浓郁激荡,大概很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,况且因为1月底爆发的疫情,海外中国人受到排挤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,恰好与《最蓝的眼睛》中的歧视主题相吻合。所以,我在讲的时候,能够不时将现实与文本粘合在一起。相比之下,《远山淡影》乍一读,显得寡淡很多。 为了调动大家的参与,在本课的微信聊天群里,我敲下了几个问题:“你觉得这本小说的主题包含哪些?”“小说中,石黑一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他者之口来讲述主角的故事?” 每次问完一个问题,我都需要等很久,有时候因为等的时间太久了,我甚至开小差地刷起了豆瓣或者知乎。这次也一样,一分钟后,一个个回答才像泡泡一样,咕嘟咕嘟地浮现在群聊里。 “战后创伤。” “文化入侵后的迷茫。” “社会变革的立场冲突。” “母女关系。” “因为要逃避过去,不愿意面对自己。” “因为要审视犯了错误的自己。” …… 如果此时坐在教室里,理想状态应该是二十多个选了课的同学围坐在一起,对小说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推敲与探讨。但此时,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,面对的是电脑发光的屏幕。我不知道每一个在微信群里发言的同学用的是哪个译本,当她或他对小说情节进行梳理时,眼神或表情会流露出什么情绪,而这些微小的表情,又会不会出卖他们对文本最真实的看法。 然而,这还并非问题的全部。这天下午,当我想要一位同学回答问题时,他像是早有预知一般,提前给我发了一条私聊:“对不起老师,我家被偷了,请不要点我回答问题,因为我在派出所做笔录。” 这个男孩我印象很深,瘦瘦的,眼镜片颇厚。大一时学教育学,上了我的大学语文的公共课后,被“诱拐”到了文学院。他爱写诗,每有大作完成就发给我看,我也从不跟他打哈哈,写得好就是好,写得不好的地方就直接说。他跟我说家在曲靖的山里,寒暑假都没法在网上买书,因为送不到。后来再跟他聊,得知丢失了一万多的现金。在农村,这可能意味着全家半年的收入。 在这节课上,他沉默了,而我当时并未意识到,他的沉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。随着网课的推进,我收到了更多的请假信息,同时也在每一堂里,看到更为显著的学生之间的表现差异。六月初,云南的疫情已经基本平稳,返校上课在即,我把所有的请假信息都保存了下来—— “老师,不好意思我无法参加下周的课,因为我家在贡山,这边发生了泥石流和洪水,家里停电。” “老师您好,一会上课时有可能你点我回答的时候我不在线,因为我家停电了,我的手机的电可能无法支撑一整天的课。” “张老师您好,明天的课我想请假,希望您批准。我这周末去转山,结果那边下大雪,我们无法回家。” “老师您好,一会上课可以不要点我吗?因为我家没网,我在村卫生所蹭网,信号不好,可能无法及时回复。但我会把大家的讨论和发言都听完的。” …… 更多时候,当我在电脑这头想要一位同学语音发言时,有一些同学会花很长时间打字,解释自己家里不方便语音,也有一些同学的语音背景里充满了嘈杂的声音:家人的喧闹、猫儿狗儿鸡儿叫、户外拖拉机突突突、店铺里的提示来客的铃声……他们总是很抱歉地在解释这些令他们感觉尴尬的背景音。这些声音像一个个窥视孔,让我得以“看到”他们所处的环境。 我精英式的培养要求与学生的就业目的之间,存在最根本的冲突 这学期,我教授西方文学史,从浪漫主义时期讲到现代主义文学。此外,我还按照自己的兴趣,开设了两门文本细读的课程,一门研读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卡夫卡、大江健三郎、伍尔夫的代表作,另一门研读诺奖作家代表作,包括托尼·莫里森、石黑一雄与纪德的作品。两门文本细读课的开设,代表了我对理想文学课的实践。 在中国基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,对文学的认识形成了一套非常顽固的模式,开口即“中心思想”,闭口即“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”。太多的思维陈规已经夺取了我们对于文学的基础感知,而文本细读——与作者的每一个字句贴身肉搏,则期待在最根本上还原被遮蔽的感受力。 上了一年多的文本细读课,我深感不易。它需要师生双方都在一个高度上获得统一。对于学生来说,至少应该熟读作品,但我发现,这项基本任务其实都完成得不尽如人意。大概由于习惯了在水课中滑水,很多人觉得读作品就等于去百度上看一下故事梗概。而网课加剧了这种不易,上网课需要高度的自律性,毕竟,不看作品甚至连老师一个责备的眼神也不会收到。所以,我与同学们展开了一场“猫鼠游戏”:为了“逼迫”大家阅读,我会随机请同学们发语音,以接龙形式复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,以此保证每个人都在听课,也都读了。 不过,同学们也偶尔会给我一个“惊喜”:“老师,还没看到这里……”甚至,“对不起,老师,我还没看……” 好吧。我应该学着接受这种落差。 这所师范院校的孩子很多来自云南本地的村寨乡镇,能考入这所一本院校,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。所谓的“小镇做题家”常常被群嘲,但能够“做题”,也已经是一种幸运。他们的成长习惯里,从不必然包含着“阅读课外文学”这个选项,哪怕阅读作品成为了进入大学后的专业工作,一种细致且主动的阅读能力普遍来说仍然是匮乏的。 所以,每个学期开学都是我的“至暗时刻”,那意味着要把许多人的阅读能力和习惯从无到有地“逼”出来。突如其来的网课,缓冲了这场猫鼠游戏的紧张感:他们不读,我也无可奈何。隔着屏幕,连不满都会削弱杀伤力,变得人畜无害。
课堂上的张秋子 图丨学生视频作业截图 可是,我又明白,表面上对学业的懒惰,其实可能是整个边陲地区基础教育的单调和刻板。所以,在每一堂文本细读的课里,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。最根本的,就是我的培养要求与学生的就业目的之间的冲突。文本细读虽然是文学院学生的基本功,但时间和精力成本极高,一个学期只能勉强读完三本小说,此外还需要大量阅读周边的传记、批评文章、论文、日记等材料,已经属于精英式的培养模式。但师范类的学生毕业后,基本上是进入中小学的语文课堂,这种类似于雕刻工一般的精细活儿,显然不适用于一篇小学语文阅读材料的解读。 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呢?看着微信群聊里不断蹦出的回答,我心里犯嘀咕。 在微信群聊里最活跃的,总是那几位。无一例外,总是家境还不错。 我带领学生们读的石黑一雄,属于那种表面上“嘴里淡出个鸟来”的作家。我很喜欢追问学生们读完文本时最直觉性、最粗糙的感觉,因为这些感觉避免了研究与理论等语言的污染,也最切近地传递出一个人感受力的高下。在周三下午的这堂网课上,我还问起了大家对《远山淡影》最直接的阅读体会是什么。有同学在群聊里说:“第一遍看完真的就是远山淡影,模模糊糊有点印象,看不真切,记不清楚。” 另一些答案也七七八八地进入了屏幕。网课要说有什么好处,那就是某种程度的“匿名性”,因为无需面对课堂上站起来发言的“暴露感”,手机或者电脑屏幕如同保护壳,让所有人都可以躲在后面勇敢地发言,而我可以在群聊中同时看到几个人在发言,然后用微信“引用”的功能,针对性地回复或者追问。 这堂课,我们聊到了《远山淡影》中石黑一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法:以无写有。通过像侦探一般一点点掘进真相,这部小说表面上讲出来的那套故事显得愈发可疑,它似乎是在以“淡出个鸟”来的口吻讲述着某些被遮掩的惊心动魄,而我们则像搜集碎片的文本侦探,整理出一条一条的证据链,拼凑出一个作家并未讲出的真相——他只是狡黠地留下来蛛丝马迹,而只读一两遍,一定会被他的障眼法蒙蔽。所以,那些隔了几十页才又出现的不起眼的细节,比如明信片、小猫、荡秋千的女孩等等,都埋着我们还原真相的证据。
张秋子用来讲网课的小说《达洛维夫人》批注 我对学生们说:“我们文本细读要做的,就是要抽丝剥茧,在表面光滑的叙事里找到那些隐藏的小缝隙,这些小缝隙将会把文本撕开一个大口子,暴露出残酷的真相。”微信聊天如果一直发语音,就会形成恐怖的语音轰炸场面,而且听与说之间都有时间延迟,所以,在很多时候,我都直接采用打字的方式授课。 当小说中女主角杀死婴儿、和公公通奸等惊人的真相一点点被还原出来时,有学生在群聊里发了感叹:“wow。”有同学说:“我去看了知网上的论文,发现很多作者都根本没看懂这个故事,就开始套各种记忆、创伤理论,而讲述的内容和小说存在完全相悖的错误!真是笑死我了。” 看到这些言论,我内心会生出一丝满足感。它可能会暂时地抵消我对这门课培养目的产生的疑虑,毕竟,它还是或多或少为学生们带来了审美或者智力上的愉悦乃至自信。 当然,如果对文本细读不感兴趣,那么上我的课估计就是一种煎熬。网课好就好在,你不用看到学生那种上课百无聊赖、低着玩手机的场景,要是不感兴趣,从头到尾不吭声就行了。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龟毛老师,如果在教室里看到一个一个玩手机的,估计都会有点受内伤。但另一些情况不仅没有被掩盖过去,反而更为暴露了。 在微信群聊里最活跃的,总是那几位。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,总是家境还不错,能够有闲钱买书看书的。在周三下午的课堂上,最活跃的女孩子,她之前就选过我的文学史,课下非常喜欢和我聊各种书和电影。这次课上,她用思维导图做了详细的人物关系谱发到群里,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有个人特色地进行阐释,甚至能够指出知网论文的硬伤。我没有具体问过她的家庭情况,但知道她是本地人,爱买书,是个影迷。每当谈到文本细节,就总喜欢用电影来进行解读。每当她在群里发言,总是显得自信笃定,侃侃而谈。 如同她谈到的《远山淡影》,她也像一个大学生活的隐秘的裂缝,撕开了一个口子,暴露出更残酷的现实。 以往,我们总觉得大家考到同一所学校、坐在同一间教室里、在同一个微信群里发言,就是平等的。但为什么有的人对各种作品如数家珍,对电影、戏剧信手拈来,而有的人却只能粗泛地谈谈老师规定的篇目,虽然每天抱着手机,但除了娱乐和综艺,并不浏览别的内容?以前,我觉得是个人天赋和兴趣或者毅力的不同,网课之后,却看到了更多的东西。 我得以拥有这些东西,本就幸运地绕过了足够多的暗礁。 六月返校后,我和他们聊起网课经历,有同学特别不好意思地说:“老师,其实好多课我都没怎么听,因为我们虽然在上课,但是父母觉得我们是闲在家里的。最近又是农忙,有时候必须跟着父母去田里去摘苞谷,而且要负责每天做家里的午饭晚饭。”还有学生跟我聊:“在我们那里,父母并不是觉得每个在家的学生只要负责好自己的学习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是边听课边做事。”甚至有同学吐露:“在家里连自己的房间、电脑、书桌都没有,还要照顾弟弟妹妹。” 其实,网课一开始,我就采用了最节省流量的方式进行。腾讯会议固然能够还原上课时即时问答的效果,但是一直开着会议,很多同学的手机流量承受不了。而且,我也有意识地避免了视频上课的方式,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并不愿意展示她或他上课的环境——比如那位连电脑和书桌都没有的同学。但这远远不够,大学水晶宫一般的环境一旦被打破,很多学生就必须面对真实的家庭环境,这种生活以其必然的操劳与嘈杂介入了学习生活。而且在价值排序中,它也因为其必须性与紧迫性,凌驾在一切学习任务之上。 当一些同学操心着家务琐事并在网络课堂里永远地沉默时,另一些同学则继续展现出他的风采,对文学的热爱、理解与灵性。网络让他们有机会不停地表达——哪怕我并没有在问他,或者并没有在问问题,他们也可以根据我谈到的内容,时不时地在聊天群里输入自己的想法——线下课堂显然不可能这样。 作为老师,这种活跃的讨论氛围,当然是我所乐见的。我们在讨论中也经常会有火花迸溅的时刻。这些课堂里令人喜悦的交锋也像是障眼法,可以让我暂时忘掉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请假的同学,以及那些永远保持沉默的同学。然而,每当一堂网课结束,我重新浏览一堂课的聊天记录,那些沉默与缺课的学生,又会像黑洞一样攫住我,而那些关于文学何为、本课何为的疑虑,也会重新浮现心头。
张秋子的书桌,疫情期间她在这里给学生上网课 大学环境是一个真空的水晶宫。它几乎抽空了学生各异的背景,一个课堂里整整齐齐坐着三四十个人,乍一看,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它的差异是隐秘的,而且常常伪装成趣味的差异:有的人爱读书、爱思考、兴趣极广、敢于表达,有的人只看老师规定的东西,而且完成的很勉强,能把自己藏起来就尽可能地藏起来。这种“趣味”的差异,很好地遮掩住了它的成因,其实,每个学生表现出的文化选择与学习能力,都是来自家庭甚至阶层文化氛围的直接结果。 农村出身的孩子务实而认真,以完成老师的规定为目的,他们并不刻意追求知识的博雅,因为他所来自的家庭并没有这种习惯;而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,几乎统一地表现出一种对智力热情的追求——哪怕不在自己的专业上,也会体现在其他“高大上”的方面,他们会选择看晦涩的塔可夫斯基而不是热门综艺,他们会选择听摇滚或者玩乐队,而不是听流行歌手,他们会读老师上课都不会提及的书……这一切,以往总是被诉诸天赋或兴趣。 网课的出现,终于把这个水晶宫打破,把这层面纱掀起。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趣味差异之下残酷的真相。这时,大学的线下课堂多少有点像石黑一雄在《远山淡影》中讲的那个表面上发生的故事,显得飘渺不实。瘟疫时期的网课,连表面的相似都做不到了,有一些人注定要缺席,手里拿着的不是书本而是刚摘下的苞谷。 那么,这个时候再问“文学何为”,应该如何解答呢?看起来很矛盾:学生们费心巴力阅读伍尔夫——一个连公交车都不屑于乘坐的精英女性——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云南的田间地头;挖空心思地解读移民作家石黑一雄,却可能连云南省都没出过。他们在四年里象征性地从事着“知识分子”的工作,但最后很大可能还是回到村镇做中小学语文老师。 在最后一堂网课上,我跟大家告别,说:“下周课堂见。”这次,似乎没人缺席。 他们开始统一格式地刷屏: “老师辛苦了,下周见!” “老师辛苦了,下周见!” …… 回到校园,水晶宫再现,远山之后的缝隙再度隐匿。我想起了最开始工作时的傻气,那时候很是偏执,总希望学生们好好考研,去个好学校大城市、好好做学术。这些年的教学经历与文学理解,反而使我坦然了,并且意识到一名优秀中小学语文老师的作用——他们远比大学老师或者所谓的“做学术”重要,他们是国民文化的基石。 而我又能教授他们什么呢?不是精英化的文本分析技巧,也不是面对文本的领悟力与热情——我得以拥有这些东西,本就幸运地绕过了足够多的暗礁,或者说,本身就不必面对凌驾于学习之上的重压。这些东西,从来只属于偶然的运气,而非个人的努力。 想了想,大概还是:好好上每一节课。(来源:腾讯谷雨实验室,文/张秋子;*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。) |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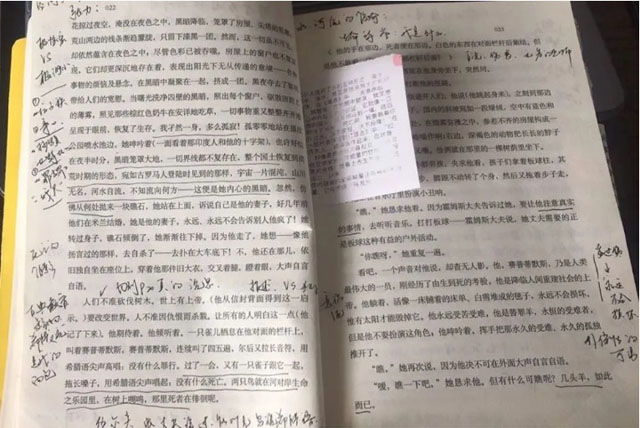


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30046号 (注:网站建设中,部分图片为样图)
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30046号 (注:网站建设中,部分图片为样图)




